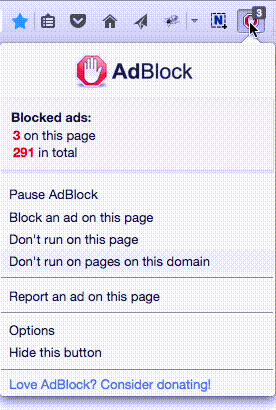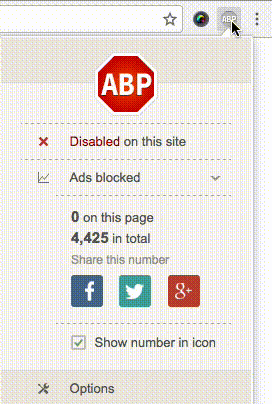人生常有这样的际遇:我们单薄的身子被挤到命运的犄角旮旯里,我们在狭小的几乎是不容回旋的局促状态中,缓缓地转过身子,退了出来,我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凭借着上帝赐予的理智、健全的神经;退不出去的就挤在了那旮旯里,挤在那旮旯里的人的神经,像是经过超常压力的挤压,改变了质素和形状,成了另种东西和另种形状,那是超常状态,非常人所能进入和理解的状态。那是慈悲的上帝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预留的一个病房,留给坚持不下去的人,让他们去歇一歇脚。
外婆就走进了这间病房,走进了另种状态。
外婆是在某个夜晚走进去的。
悲剧大多选择夜晚发生。
夜晚,外婆起身,跪在床头,举着毛主席语录本,对着毛主席像说,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她说这番话时用的是湖南口音。她不断地这样说这样做,惊醒了母亲,母亲就起身劝她重新睡下,过不了多久,她又这样做,母亲又起身。那个夜晚,她的不断坚持和母亲的反复劝说,就形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劝说的母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比方说,“明天我还要上班,你老人家就可怜可怜我,睡吧”。外婆没有争辩,过不久她又起来。在无数次的拉锯战之后母亲终于认输,对我说外婆怕是疯了。这是个电光火石般的句子,也是母亲在不耐烦和受不了时,不经意触摸到的事实。这句话一出口,在说者和听者心里,不啻是霹雳贯空焦雷当顶。用湖南话说是,打个炸雷。
外婆疯了。
外婆疯前极为善良,疯了的外婆也没有破坏力,只是固执。她固执地挪动着她的箱子,她想回她的老家去。她的老家在南方,由于种种原因,她像颗树一样,被移植到北方。北方有她不习惯的饮食,有她听不惯的方言,这里不吃她泡制的茄子干,邻居们吃了一片含在口里,一边说好吃好吃,一边走出门腾出空就把它吐了;这里听不懂她讲的话,她跟对方讲半天,无异鸡同鸭讲。她总是生气地回来说,未必我讲的就不是中国话,咯也不懂!这些事情这些时刻都使她想回家去,但是她好的时候,她从来不说。她像颗树一样,被移植到了北方,她就站立在北方的天空下;她像个战士一样,听命于战事的需要。
外婆一直像个听命于需要的战士,她选择了她的儿女中生活条件最差最苦的那家住下,那便是我们家。她在我们家洗衣煮饭,这时,她褐色的皮箱就在她的床头,里面永远清清爽爽地叠了她的换洗衣服,黑是黑白是白,永远那么简洁也简捷,仿佛随时可以拎起箱子就走,可是她一直未能走。
其实她一直想去南方,其实她不是战士,她只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平凡瘦弱的湖南老年妇女,她爱吃湖南菜,想听乡音。但是生活要求她在老年的时候依然要扮演一个过重的角色,无论她多么地不适应多么地想家,无论她多么地老和多么地累。现在不同了,现在她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她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她现在想的是回家。
她拿不动箱子她只能够挪箱子。每个人都来阻拦她,用花言巧语骗她劝说她,外婆不相信。疯了的外婆表现得比清醒的时候还要有主张有见识,还不轻易上当。外婆弱小的身子抱着树,脚下是她的箱子。我也只有那么小,我也隔着树劝她,我的眼睛与她对视,我在我的眼睛里灌注了无限的痛惜和柔情,我希望她能够看到,能够理解并且接受。外婆显然没有理解也没能接受,她依然美丽的眼睛里一片空泛,还有就是受了伤害之后的惊恐。这空泛和惊恐让我再度明白,外婆是在另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离我们很远,常人是走不进去的,痛惜和柔情也同样走不进去。
那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于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件事,将外婆逼到了绝境。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没有了是非对错和好坏善恶之分,还随时随地发生批斗武斗枪击打砸抢“五湖四海”等。“五湖四海”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周游的打砸抢队伍,名字取自于领袖的一句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一切,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年迈的老婆婆理解?
母亲和二哥,他们是我们这个家庭挣钱拿工资的人。他们以挣钱拿工资的人才有的资格和成熟,听取和接触着外面世界,并将之带回家来。他们忍不住用恐怖得兴奋以致亢奋的声调,交流和交换着各种大道和小道的消息,然后是彻夜地分析形势和商量对策。为防止其他的家庭成员听到惹出祸端,他们在讲述的时候,用隐语用眼神用小心翼翼。听了他们的切切私语,令你想到密室想到非法组织和白色恐怖之类。相信在那些个白天和夜晚,你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听到,但你一定获得了远远大于他们的恐惧,陷入了巨大的无可名状的恐怖之中。他们还无休无止地折腾着家里的那点破烂,把乌克兰皮大衣用剪子从中间冲开;把绣有龙凤的被套枕套剪烂铰碎,半夜丢到垃圾堆里去;把装有所谓细软的箱子藏在床底下,外面用一堆破劈柴将它们挡住;一会儿又将它们取出来,分散了放到天花板上,放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如何要防老鼠以及防霉变,然后再将洞口封好用石灰糊上,企图让外人一眼看不出来。然后就是对家人进行战前动员和防范教育,比方说有抄家的来,不要往天花板上看,要尽量引开他们的注意力等等。其实,天花板上那点事儿,除了安慰安慰他们十分赤裸的恐惧之外,什么也瞒不住——新搪的石灰与原先的天花板的模样,永远是两回事。
母亲反复强调,家里不得带回粉笔来,不得有乱写乱画行为,开会时最好不要发言,非发言不可时就说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母亲说这话时因激动和亢奋而显得咬牙切齿,脸上显出病态的潮红。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和向纵深发展,母亲就进了对敌专政学习班。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母亲就去了学习班。学习班有好多种,如狠斗私字一闪念学习班,继续革命学习班等,而对敌专政学习班在级别上属于最高形态,距公检法恐怕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母亲进这个学习班,从她曾经的右派身份和父亲至死都是右派的身份这点来看,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在这个学习班里,母亲享受着全封闭的学习待遇,集体行动,无论是学习还是吃饭,全排着队唱着歌来唱着歌去,没有私人空间,没有单独行动,更不能回家。外婆如果想看到母亲,就只有在吃饭时候到饭堂门口,隔着大铁栏杆门去看。母亲不能随意走动,只有蹲在院子中间的地上,边吃饭,边隔着饭堂那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院子,向她的母亲频送目光。一天当中,一对母女也只有这个时间才能够相互用目光关照着彼此。如果从铁栏杆门的两边看去,两手抓住铁栏杆门的外婆和她的凄切神态,与探监没什么两样。
说来说去,这事还是透着恐怖。恐怖深不见底。
有专家认为,人们恐怖自己所不理解的东西。外婆,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老年妇女,她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多少呢?不理解就害怕,就想逃离,她又能逃离到哪里去呢?全国山河一片红,神州大地尽文革,她所有的儿女都无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难以自保,更何况,她的战斗岗位还在这里,在她一心想挽救想尽微薄之力的女儿家。这样,她就被挤兑到人生的犄角旮旯里了,她走进了那个病房,走进了另种状态。
外婆走到另种状态里,她反复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向毛主席请安、献忠心;二是挪她的箱子,她想回家。可见那个世界与我们并不遥远;同时也可见,外婆虽已精神失常,依然是那么的目标坚定矢志不移,丝毫不被正常世界里的人所欺瞒所误导,不被繁琐生活的细枝末节所阻挡所搅和,显示出这两件事在她心里的份量。这两年事是她从正常世界带去的,是她在正常世界时的日思夜想,是用心血浇灌并随着岁月生长的。前者是祷告祈福,为她罪孽深重的儿女们——假如他们真地有罪的话;后者,为自己。这是她今生今世要做的两件事,哪怕是在另种状态里。
这令我想起李慧娘的故事。舞台上,变成鬼的李慧娘穿着白色的衣裙美丽地舞着,表达她的爱恨情仇,至情至义,那么直接地做她生前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