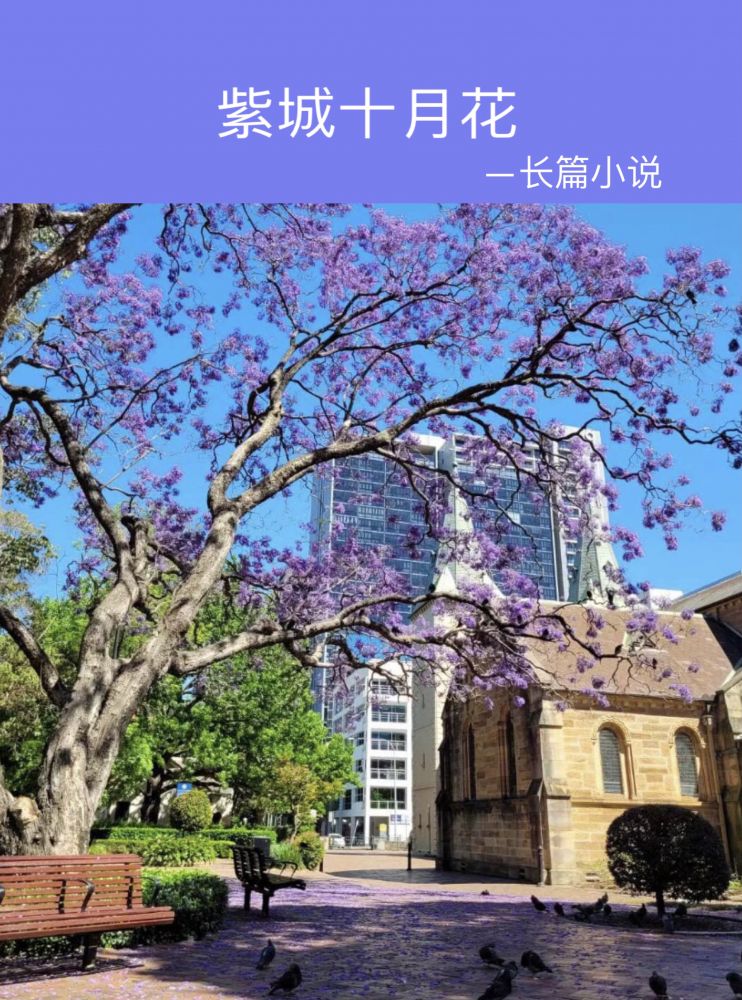
淑君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她把手提包往桌上一扔,整个人瘫软在沙发上,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虚脱无力。她闭目养神地呆坐了五分钟,然后把走累的双腿搁在一张靠背椅上,身子继续懒洋洋陷在沙发里,这是她喜欢的一种减压方式,对消除疲劳行之有效,可今天淑君却觉得不大对劲,身子安放好了,心绪却乱成一团,捉摸不定,像风一样变幻莫测,像云一样上下翻卷。
她干脆睁开眼睛,强打起精神,眼光却无意中落在了穿衣镜上。出门前自己还在镜子前开心的左顾右盼,可回来时却是一副惘然若失的样子,整个人就像玩过山车似得心绪难平,当然这些变化仅仅发酵于自己的内心,外表看起来并没有多大改变。现在摆在淑君面前的只有二条路,要么听任这些蠢蠢欲动的冲动自生自灭,要么准备迎接一场家庭风暴的来临。
家里安静的出奇,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冯子健带着儿子去他爸妈家里,这是他们父子俩每个星期的例行公事。每当这个时候,淑君总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
太阳从西边斜斜照了进屋内,霸占客厅的一角,明晃晃的十分刺眼。淑君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屋内的光线顿时柔和了许多。当她转身想坐回到沙发上时,忽然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引起她的注意——这是淑君和冯子健两人的结婚照。淑君伸出右手,扶了扶墙上的相框,然后仔仔细细端详着自己的结婚照。岁月如流,感今怀昔,那天淑君笑的很灿烂,一身紫红色绸缎连衣长裙,一头秀发烫成长波浪卷发,瓜子脸,二道浅浅的柳叶眉下是一双美丽的眼睛,明眸皓齿,楚楚动人。冯子健穿一套藏青色毛料西装,一头齐整短发,五官端正,英俊潇洒。初看起来,俩人颇有夫妻之相。
自从五年前嫁给冯子健,淑君对人生的追求似乎走到了尽头。每天朝九晚五之后,剩下的尽是些单调乏味,千遍一律的时光,面对的是一成不变的人,一成不变的语言,一成不变的生活,还有一成不变的未来。淑君有时回想起自己结婚之前,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岁月,天资聪颖,却又勤奋好学;朝气蓬勃,却又脚踏实地;无忧无虑,却又怀揣梦想。唉!夙心往志,都成了过往云烟的回忆。
现在的淑君谈不上快乐,也说不上不快乐,一切都是平平淡淡,一潭死水。没有梦想的生活了无生趣,再好的锦衣玉食都变得令人生厌。有时淑君也会扪心自问,冯子健到底在哪方面有吸引力?对于这个问题,她至今也答不上来。冯子健是个顾家的好男人,好男人等不等于好丈夫?人如饮水,冷暖自知,只有她自己方能领略。
别的不用评说,光说人的境界,冯子健简直跟弄堂里的大叔大妈同一个层次。每天早上,他从菜市场买菜回来,必定在弄堂里跟东家的大妈扯一通闲话,同西家的大叔聊一会儿家常。话题自然离不开菜市场上鱼有些什么品种,肉、蛋是什么价格,又有哪些新近上市的蔬果,俨然像是一个菜市场的小广播站。有的时候,他甚至还当起了"长舌男",东家长,西家短,飞短流长,惹出不少口舌。气得淑君只好把挂满衣服的竹杆往晾衣架上重重的一放,这里淑君生气的信号。所以冯子健只要看到自家的"彩旗"高挂窗前,就会立马悻悻然的赶紧回家,到了家里,他也闭口不谈刚才的事情,否则准会迎来淑君怒不可遏的眼光。
按理说有了儿子后,夫妻之间的话题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变得多起来,但事实却相反,现在他们在生活上越是接近,心理上的距离反而越远。在外面,冯子健还是改不了爱吹嘘炫耀的毛病,结婚之前他喜欢说他的家史,他的职业。结婚后就改成谈论做医生的老婆。现在的话题则更多转移到自己的大胖儿子身上,逢人便讲,儿子的眼睛像奶奶,鼻子像爷爷,嘴巴长的像阿姨,皮肤细腻的更像他自己,儿子的整个人都成了他们冯家的复制品。回到家里,这位老兄只是把淑君当作一个高高在上的玩偶,连看妻子一眼都用他惯常的眼角余光,说话也是一副怕说错话的样子,平铺直叙,见解庸俗,尽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讲话内容空洞,乏善可陈,如同行人天桥一样的平淡无奇,没有一丁点儒雅气度可言。淑君有时后悔的想,我怎么就没找个稍微有点幽默风趣的男人?通向心灵之路总该有满树的繁花,此唱彼和的鸟鸣。
对于自己的丈夫,淑君还没想好该怎么向他开口,但不管以何种方式提出,自己心里总得先有个大致方向。
佳丽的提议,一开始让淑君吃惊不小,它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淑君尘封已久的渴望,那种深藏于心,梦中萦绕的梦想一下子清晰展现在淑君面前,反而让她瞻前顾后,裹足不前。然而经过一番沉思默想后,淑君理顺了自己的思路,对于出国留学有了清晰的看法。
首先,如果不出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基本上都能猜出个十之八九。世上最能扼杀个人意志的莫过于这种雷打不动的稳定,大姐要是没回沪,她依然雷打不动的在江西插队务农,一辈子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如果没有恢复高考,自己雷打不动不知被分配到哪一个角落,靠着仅有的一丁点的眼界,一丁点的见识,浑浑噩噩虚过一生。而出国留学,人生的际遇会大大改变,存在着无限的可能,当然也会有理想与现实背离的事情发生,但是不走出去,你哪会知道你的人生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
其次,出国留学,不仅给自己一个从新开始的机会,也为下一代开启一扇机会之门,既然把自己的孩子带来这个尘世,就得尽自己所能为孩子谋个光明的前程,这是每个做父母的自然而然的责任。在国内不要说小孩竞争的起跑线不公平,终点线也不一样,有没有出息,大部分靠孩子的投胎造化。而出国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公平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参与竞争,至于是否出人投地,全凭孩子的努力。所以出国与其说为了自己,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孩子,而这种机会很多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谓的把握机会就是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最后,现如今出国留学行情看涨,在一片上"涨"的行情中,个人的人生目标更加容易达到,尤其是自己还年轻,有干劲,有学识,就是从头再来也能拼上三十年。自己已经虚掷了一半的大好时光,为什么不把另一半的年华留给外面的世界?至于说冯子健的态度,凭淑君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只要这笔学费不是从他腰包里掏出来的,应该问题不大,事情一旦牵扯到钱,那他准跟你掰扯出个子丑寅卯来。
冯子健的反应并没有太出乎淑君意料,他只丢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说:"我们家除了你以外,看不出还有第二个人有勇气跨出这一步。"他的这番话是褒奖,还是贬损?外人听来一定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然而淑君和冯子健生活这么多年,她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你这一步跨出去之后,一切后果自负。还好学费是从佳丽那里借来的,要不然这句话后面一定还跟着一大堆难听的话。
冯子健爱钱更甚于爱淑君。他生活上精打细算,买东西根本用不着淑君来操心,从不会吃亏上当。他关心淑君可以做到无微不至,但在言语上永远是那种不温不火,就像是隔夜保温杯里的温开水。淑君现在正需精神上的慰励,需要家里的慰安与温暖,不管是鼓励她勇敢的走出去,还是怜爱她留在家里,淑君都会感激不尽。要还是个男人就该拍拍自己肩膀说,这副担子应该由我一肩挑。淑君多么的想倚在他身边,多么的想伏在他肩头,多么的想得到他的摩抚,那怕是片刻的休憇,短暂的宁神,稍许的欢愉。而淑君面对的却是无情和冷漠,现在淑君真正体会到冷谟就像一把利刃,可以戳破她编织的任何美梦。
如今唯一令淑君不舍的是儿子宽宽,这孩子长的浓眉大眼,聪明伶俐,十分讨人喜欢。如果自己就这么一走了之,接下来便有一大堆后续的问题。早期教育倒不用太担心,反正孩子的爷爷奶奶都是退休教师,他们自有一套教育小孩的方法。剩下最大的问题是母爱对孩子心灵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当然这决无可能去量化分析,但长期的影响肯定存在。怎么办?还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没有,完全没有!除非放弃这次出国机会。
淑君陷入了痛苦的内心挣扎,周围的人只关心出国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可有谁来聆听自己的心声?那种冷漠冰冷的世俗目光,那种母子的离别之痛,只有事到临头的淑君才能真正的体会。当初《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若是有自己的孩子,她会不会还选择离家出走?或许她根本不会,连易卜生也屈服社会的压力而更改结局。三十年代娜拉曾影响过老一代上海女性,半个世纪过去了,上海女性追求自我觉醒的步伐依旧还是那般的热切,淑君身边许多结了婚的女性正毅然决然地投入出国的潮流之中,她们是新时代的娜拉。
淑君完全是一个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她有权拒绝道徳绑架,她更有权追求自己内心的呼唤,每个人都活这短短的一辈子,难道女人都得遵从男人的意愿,男人的安排。世界是那么的精彩纷呈,很多对与错的认知,"我得自己思考然后去了解"这是淑君的心声,更是新一代知识女性的追求,她们不仅要走出家庭,还要与男人平分秋色,甚至比男人走得更远。
淑君深感自己近年来变化很大,当年的雄心壮志早已消磨殆尽,意气奋发也不复存在,柔情蜜意更是灰飞烟灭。舒适的家庭,坚如磐石的稳定,淑君溺于其中而陶陶然,其实带给她的是消沉和迷茫。淑君快到了连自己都嫌弃自己的地步,"你以前并不是这样,你早早挑起家里的生活担子,能力和眼界都比我们同龄人高出许多。"佳丽的话又回响在耳边,或许还有佳丽最了解自己。真的要紧紧抓住这次改变命运,脱胎换骨的机会,或许这是自己人生最后的一次选择。
经过二个星期的沉潜静思,权衡利弊,淑君终于下定决心,出国求学。她先去医院开个办理户照的证明,接着去办理各类的公证文件,然后委托佳丽熟识的留学代理,顺利拿到了澳洲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她把这些材料汇总后邮寄到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接着就满怀期待地等待签证。可天有不测风云,淑君的申请看似一切顺利,千里之外的北京却爆发一场浩浩荡荡的学生民主运动,接着西方驻华使馆纷纷撤离北京,淑君的学生签证申请也跟着一起石沉大海。
原创作品,未经许可请勿转载,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