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日,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看到2023年12月30日纯粹Pura推送的《张炜:我们不是把陶渊明推到反抗者的风口浪尖,就是把他推下个人闲适的田园洼地里去》后表示:“我完全同意张炜的观点!我也写过一篇关于陶渊明的文章,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之后,孙康宜教授说:“最近读到你们纯粹发出的张炜有关陶渊明的文章,很高兴!其实有关陶渊明的复杂性,我曾经于2001 年发表过一篇题为《陶潜的经典性与读者反应》的文章,也登载在你们为我出版的“孙康宜作品系列”的《长亭与短亭》 那一册。如果纯粹Pura也能以微信的方式与读者分享,将会很有意思。”孙康宜,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曾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耶鲁大学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荣休讲座教授。在西方汉学界备受推崇,在国内学术界享有盛誉。孙康宜作品系列,2022年7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出版,全系列共5卷,现已出版《千年家国何处是:从庾信到陈子龙》《长亭与短亭:词学研究及其他》《独行的缪斯:自传、性别研究及其他》3卷。孙康宜作品系列集中西文化之精华,角度独特,重新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种面向、内在结构和文化生成原理。其中,《长亭与短亭:词学研究及其他》是一部孙康宜教授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著,内容广博。其中尤为精彩的是对词学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的方法、思路、观点相比均别开生面,注重学理和文本本身层面进行梳理和分析。收录专著《词与文类研究》及《“古典”与“现代”:美国汉学家如何看中国文学》《柳是对晚明词学中兴的贡献》《汉学研究与全球化》《阴性风格或女性意识》《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内容广涉孙康宜的词学综合研究成果、对中西经典文学及中西文学比较方面的心得和洞见、边缘论题、最新探索的生荒领域等。其中,对中国古典作家的审美追求、中国古代女性作者的地位问题等,均做了饶有趣味、角度独特的探讨,从中可以窥见孙康宜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研究成果。
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说,伟大的作家总是那些“简直就是压倒传统并包罗它的人们”[1] 。陶潜这位曾多少个世纪以来激发起文学史家研究兴趣的中国传统中最早的诗人之一,正是这样的一位诗人。陶潜一生才写了约150首诗、10篇文与赋,在当时的文坛上又是一个边缘人物。他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居然能占有如此重要的经典位置,这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在文学史上他的经典化的一个关键时刻,就在于苏轼宣称陶潜是一位空前的大诗人,以及方回称赞陶潜和杜甫为两位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至圣先师[2]。在清代,顾炎武和朱彝尊等人也都啧啧称赞陶潜的成就。王士祯在其《古诗选》一书中还特别指出“过江以后,笃生渊明,卓绝先后,不可以时代拘限矣”,可见其评价之高[3]。 后来20世纪初期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则将苏轼也列入了这个伟大作家的行列,同时梁启超遴选出陶潜和屈原(第一位有名有姓的中国诗人)为两位发出诗人最强音的文学巨擘,王国维也在同时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的《文学小言》中,王国维说:“屈子之后,文学之雄者,渊明其尤也。” [4]确实,不管这些经典作家的名单包含哪些人,陶潜的名字总会被列入。多少个世纪以来,有关陶潜的学术研究汗牛充栋,以至于一个特殊的术语“陶学”也被炮制出来,与“诗经学”“楚辞学”和“红学”遥相呼应[5]。直至今日,读者阅读陶潜的热情丝毫不减,都在声称重新发现了诗人真正的声音。 然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陶潜的不朽,而事实上我们对于诗人却又知之甚少呢?甚至在今天,我们仍无法确认他的本来的姓名。不幸的是,最早的有关陶氏的传记都各自给出不同的名字——或是陶潜字渊明;或是渊明字符亮;或者就是元亮,又名深明。其中最有趣的是,《晋书》的编者干脆就略去“渊明”这个陶氏所为人耳熟能详的名字[6] 。至于陶氏的生日,则更是扑朔迷离,正如1996年出版的一本题为《陶渊明悬案揭秘》的书一开头所问的:“出生哪一年?”[7] 尽管事实上大多数学者都赞成公元365年为其生年,仍有一些学者(如梁启超)坚持372年应为定论[8] 。还有一些学者给出了376年或369年等等,全在宣称他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之上的[9]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因为陶氏生平事迹的确切日期的付之阙如,才会有如此多的年谱应运而生,都在试图将陶氏的生平与作品予以精确化。有关这些年谱的种类之繁多,戴维斯(A. R. Davis)——陶潜研究最知名的学者之一——这样说:这一奇特的中国治学法有着内在的过于精确的倾向……我所要反复说明的是这是不正确的,而且我之所以在此指出这种广为人知的论点的缺失,并提出研究年代精确性的不可能,乃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会为陶潜研究带来一定的好处。[10] 不管怎样,这一“系年确定性”之阙如凸现出陶潜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诗人的名微反映了他在魏晋社会中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在我的《六朝诗研究》一书中,我已经解释了陶氏作品不为时人所赏且为后人所误解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平淡诗风,从他那时代的风气来衡量,缺乏华艳的词藻[11] 。不过,我以为陶潜的名微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时人眼里基本上是一位隐士,在仕宦生涯中是一个边缘性的人物。在六朝时代,正如左思所言:“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于是乎那些与朝中官宦殊无瓜葛的人士便注定了难以扬名。虽说陶潜的曾祖父陶侃也是建立东晋的有功之臣,但早在陶潜降世以前其家境便久已式微。当然,陶潜一生中的最后20年也是在隐退中度过的,这也难以为他的社会地位增添荣耀。诚如陶潜在其传记素描《五柳先生传》所言:“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遗憾的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一文——那是仅存的由当时人所写的有关陶潜的篇什——很少留下有关陶潜生平的确切年代或事实资料。正如戴维斯所提出来的,这些人物逸事“或多或少有几分夸张,有时刻意追求逼真的效果,反失之于可疑”[12] 。同样,王国璎也注意到某些被保存在正史中的有关陶潜的重要逸事——包括有一则提到陶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都是基于一些不牢靠的记载[13]。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逸事只不过是传闻而已,而沈约——《宋书·隐逸传》的作者,拿它们主要用来增强戏剧效果。后来,《晋书》编者房玄龄和《南史》编者李延寿都在他们有关陶潜的传述中沿袭了这种说法。事实上,他们又擅自在自己的篇目中添油加醋,也许是意在将陶潜塑造成一位高士。应当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陶潜的传记都出现在“隐逸”类目。也就是说,传记编者自己更关注陶潜作为隐士的“公众”形象(与《隐逸传》中的其他人物一致),而不是陶潜作为诗人的“私人”的一面[14]。例如沈约的《隐逸传》,对陶氏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陶氏作为一个诗人这一事实不知为何给遗忘了。显然,陶潜的道德人格及其作为一个隐士的政治角色是这些官修史书的关注焦点。作为“浔阳三隐”之一,陶潜被拿来代表隐士的典型,代表坚贞不渝地拒绝出仕、弃绝世俗价值的典范人物。由此可见, 通读断代史的《隐逸传》,我们可以发现无数个遭遇和心态与陶潜相仿的个人事例[15] 。事实上,陶潜家乡邻近地带素来以隐士称誉,世代相传[16]。特别是陶潜在《桃花源记》中所称颂的刘遴之,在《晋书》中几乎与陶潜齐名[17]。刘遴之也像陶潜那样,在原则上毫不妥协,拒绝出仕。刘氏的生活起居俭朴自立,不慕名利而怡然自乐,也颇似史传中的陶潜。如此完美的隐士形象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他们反映了中国人所面临的人生出处的大问题,也就是:如何来看待正直的精神和污浊的官场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途径,自然是炮制出在污浊的世界中始终能寻求心地平和、能体现历史人物风范的这样一个榜样。于是,在史书记载中所发现的陶潜,充当了一个模范人物,其个体性与传统隐士的典型性正相吻合。正如颜延之在追怀陶潜的《陶征士诔》中所云:陶氏“廉深简洁,贞夷粹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陶潜只被当作道德楷模而其文章却鲜为人知——至少在他身后一百年里还是如此。
然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陶潜的不朽,而事实上我们对于诗人却又知之甚少呢?甚至在今天,我们仍无法确认他的本来的姓名。不幸的是,最早的有关陶氏的传记都各自给出不同的名字——或是陶潜字渊明;或是渊明字符亮;或者就是元亮,又名深明。其中最有趣的是,《晋书》的编者干脆就略去“渊明”这个陶氏所为人耳熟能详的名字[6] 。至于陶氏的生日,则更是扑朔迷离,正如1996年出版的一本题为《陶渊明悬案揭秘》的书一开头所问的:“出生哪一年?”[7] 尽管事实上大多数学者都赞成公元365年为其生年,仍有一些学者(如梁启超)坚持372年应为定论[8] 。还有一些学者给出了376年或369年等等,全在宣称他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之上的[9]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因为陶氏生平事迹的确切日期的付之阙如,才会有如此多的年谱应运而生,都在试图将陶氏的生平与作品予以精确化。有关这些年谱的种类之繁多,戴维斯(A. R. Davis)——陶潜研究最知名的学者之一——这样说:这一奇特的中国治学法有着内在的过于精确的倾向……我所要反复说明的是这是不正确的,而且我之所以在此指出这种广为人知的论点的缺失,并提出研究年代精确性的不可能,乃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会为陶潜研究带来一定的好处。[10] 不管怎样,这一“系年确定性”之阙如凸现出陶潜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诗人的名微反映了他在魏晋社会中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在我的《六朝诗研究》一书中,我已经解释了陶氏作品不为时人所赏且为后人所误解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平淡诗风,从他那时代的风气来衡量,缺乏华艳的词藻[11] 。不过,我以为陶潜的名微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时人眼里基本上是一位隐士,在仕宦生涯中是一个边缘性的人物。在六朝时代,正如左思所言:“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于是乎那些与朝中官宦殊无瓜葛的人士便注定了难以扬名。虽说陶潜的曾祖父陶侃也是建立东晋的有功之臣,但早在陶潜降世以前其家境便久已式微。当然,陶潜一生中的最后20年也是在隐退中度过的,这也难以为他的社会地位增添荣耀。诚如陶潜在其传记素描《五柳先生传》所言:“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遗憾的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一文——那是仅存的由当时人所写的有关陶潜的篇什——很少留下有关陶潜生平的确切年代或事实资料。正如戴维斯所提出来的,这些人物逸事“或多或少有几分夸张,有时刻意追求逼真的效果,反失之于可疑”[12] 。同样,王国璎也注意到某些被保存在正史中的有关陶潜的重要逸事——包括有一则提到陶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都是基于一些不牢靠的记载[13]。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逸事只不过是传闻而已,而沈约——《宋书·隐逸传》的作者,拿它们主要用来增强戏剧效果。后来,《晋书》编者房玄龄和《南史》编者李延寿都在他们有关陶潜的传述中沿袭了这种说法。事实上,他们又擅自在自己的篇目中添油加醋,也许是意在将陶潜塑造成一位高士。应当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陶潜的传记都出现在“隐逸”类目。也就是说,传记编者自己更关注陶潜作为隐士的“公众”形象(与《隐逸传》中的其他人物一致),而不是陶潜作为诗人的“私人”的一面[14]。例如沈约的《隐逸传》,对陶氏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陶氏作为一个诗人这一事实不知为何给遗忘了。显然,陶潜的道德人格及其作为一个隐士的政治角色是这些官修史书的关注焦点。作为“浔阳三隐”之一,陶潜被拿来代表隐士的典型,代表坚贞不渝地拒绝出仕、弃绝世俗价值的典范人物。由此可见, 通读断代史的《隐逸传》,我们可以发现无数个遭遇和心态与陶潜相仿的个人事例[15] 。事实上,陶潜家乡邻近地带素来以隐士称誉,世代相传[16]。特别是陶潜在《桃花源记》中所称颂的刘遴之,在《晋书》中几乎与陶潜齐名[17]。刘遴之也像陶潜那样,在原则上毫不妥协,拒绝出仕。刘氏的生活起居俭朴自立,不慕名利而怡然自乐,也颇似史传中的陶潜。如此完美的隐士形象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他们反映了中国人所面临的人生出处的大问题,也就是:如何来看待正直的精神和污浊的官场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途径,自然是炮制出在污浊的世界中始终能寻求心地平和、能体现历史人物风范的这样一个榜样。于是,在史书记载中所发现的陶潜,充当了一个模范人物,其个体性与传统隐士的典型性正相吻合。正如颜延之在追怀陶潜的《陶征士诔》中所云:陶氏“廉深简洁,贞夷粹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陶潜只被当作道德楷模而其文章却鲜为人知——至少在他身后一百年里还是如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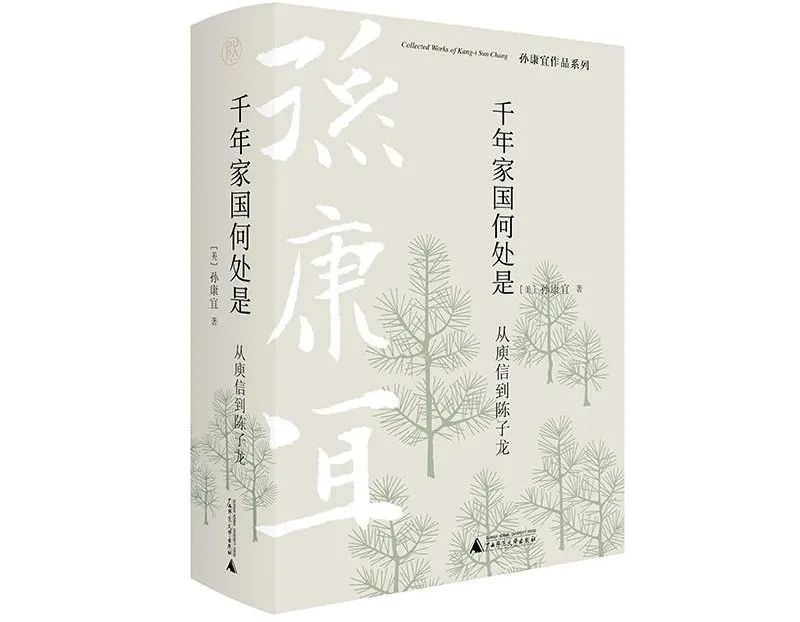 然而,一旦阅读陶潜的诗作,就会发现另一个略有不同的陶潜,他绝非传统史书编纂者所塑造出来的单一人物。有好几位现代学者指出了这一点。例如,戴维斯提到人们“从陶氏作品中所获得的印象很不同于从早先史书传记的逸事中所得出的印象”,因为在后者中诗人自己的“矛盾不一的姿态”常被扭曲[18]。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注意到陶氏的诗歌“充满了矛盾,而矛盾出自一个复杂而富有自觉意识的人却渴望变得不复杂和不自觉”[19] 。近年来,台湾著名学者王国璎凭其细读陶潜,“发现”了远比先前所体会到的更复杂而有趣的人格。她进而观察到,尽管陶氏为他当隐士的慎重抉择而引以为豪,但他绝非没有片刻怀疑过这个抉择[20] 。最显著的是,在他的《与子俨等书》(据说是陶氏的遗嘱)中,陶潜为他的子辈在孩提时代饱受饥寒表达了相当的内疚。诗人还痛心于他的妻子未能像老莱子之妻那样全心支持她丈夫的隐士理想,甚至劝阻他出仕[21] 。陶潜的自白全然不同于萧统的《陶渊明传》将其妻描绘成陶氏的良伴[22] 。而这样富于洞见的比较始终未能引起关注,直至近来学者才开始细读陶潜的作品。诚然,所有这些现代新读法都在促使我们挖掘陶氏诗中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明了人性的复杂。我们发现,与常规传记所描绘的简单化的陶潜形象有所不同,陶潜自己却有意向他的读者传递众多有关他自己的信息——包括他一生中重要事件的具体日期、朋友的名字、他解甲归田的动机、个人的忧惧与困扰、自嘲的性情等等。最重要的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多样,就其诗歌所能把握的而言,总是将我们导向诠释陶潜的不确定性。当现代学者钟优民说“陶渊明说了1500多年,迄今仍是长议长新,永无止境”时,他所指的正是这种诠释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构成了陶潜研究的一个特征[23]。然而,这样的认识,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解读之后才达成的,它喻示了从单纯的道德评判向陶氏作品的文学性和整体性欣赏的逐渐转型的完成——它包含了美学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解读。
然而,一旦阅读陶潜的诗作,就会发现另一个略有不同的陶潜,他绝非传统史书编纂者所塑造出来的单一人物。有好几位现代学者指出了这一点。例如,戴维斯提到人们“从陶氏作品中所获得的印象很不同于从早先史书传记的逸事中所得出的印象”,因为在后者中诗人自己的“矛盾不一的姿态”常被扭曲[18]。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注意到陶氏的诗歌“充满了矛盾,而矛盾出自一个复杂而富有自觉意识的人却渴望变得不复杂和不自觉”[19] 。近年来,台湾著名学者王国璎凭其细读陶潜,“发现”了远比先前所体会到的更复杂而有趣的人格。她进而观察到,尽管陶氏为他当隐士的慎重抉择而引以为豪,但他绝非没有片刻怀疑过这个抉择[20] 。最显著的是,在他的《与子俨等书》(据说是陶氏的遗嘱)中,陶潜为他的子辈在孩提时代饱受饥寒表达了相当的内疚。诗人还痛心于他的妻子未能像老莱子之妻那样全心支持她丈夫的隐士理想,甚至劝阻他出仕[21] 。陶潜的自白全然不同于萧统的《陶渊明传》将其妻描绘成陶氏的良伴[22] 。而这样富于洞见的比较始终未能引起关注,直至近来学者才开始细读陶潜的作品。诚然,所有这些现代新读法都在促使我们挖掘陶氏诗中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明了人性的复杂。我们发现,与常规传记所描绘的简单化的陶潜形象有所不同,陶潜自己却有意向他的读者传递众多有关他自己的信息——包括他一生中重要事件的具体日期、朋友的名字、他解甲归田的动机、个人的忧惧与困扰、自嘲的性情等等。最重要的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多样,就其诗歌所能把握的而言,总是将我们导向诠释陶潜的不确定性。当现代学者钟优民说“陶渊明说了1500多年,迄今仍是长议长新,永无止境”时,他所指的正是这种诠释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构成了陶潜研究的一个特征[23]。然而,这样的认识,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解读之后才达成的,它喻示了从单纯的道德评判向陶氏作品的文学性和整体性欣赏的逐渐转型的完成——它包含了美学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解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陶潜是为他的读者所塑造出来的;如果我们采纳哈罗德·布鲁姆有关大作家影响力的理论[24],或许我们甚至会说在某种程度上陶潜塑造了中国人。在过去的数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解读陶潜来塑造他们自身,以至于他们常常拿陶潜的声音来当作他们自己的传声筒。而且,在陶潜身上有如此多的“中国性”,尤其是在漫长的解读陶潜作品的过程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宣称陶潜对于文化史的总体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无须说,要追溯陶潜经典化的漫长历史以及陶潜作为一个经典化的诗人在中国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本文中我只想强调陶诗解读史中几个有助于揭开诗人面具的方面。诚然,假如我们把早期的传记作品当作一种“面饰”——有鉴于它们倾向于过分强调陶氏作为一个隐士的单纯——那么我们也许会说后起的陶诗读者在其根本上是揭开陶氏的面具。他们通常渴望发现陶氏的真正的自我——揭露他作为一个有隐情和焦虑的真正的个体,以便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毫无疑问,其中某些解读并不完全牢靠,然而正是透过这些解读(无论其正确与否),所谓的“陶学”才得以成形,最终构成了陶潜之谜。陶潜最为人所喜爱的形象之一便是嗜酒之士。传说每有宾客来访,陶潜必邀之共饮。确实,据沈约的《宋书·隐逸传》,若陶潜已醉在先,他便会直言告诉宾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沈约《宋书》所录的另一则脍炙人口的逸事(可能是源于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则进一步说明了陶氏的饮酒以及他与江州司马王弘的交谊。这则故事说陶潜于九月九日重阳节无酒,便出门在其宅附近的菊花丛中久坐。有顷王弘携酒而至,两人饮至酩酊大醉[25]。这些逸事只是谣传而已,编造出来也许只是要强调陶潜作为一个隐士的任诞的性格。然而,正是这些不很可靠的来源才成了最重要的背景,被后代的批评家拿来解读陶潜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九日闲居》一诗,批评家在笺注该诗时几乎一致地援引王弘一事。这样的一些解读方法会被质疑,可是仔细对照陶潜自己的作品,我们当然也会产生一种诗人是酒徒的印象。在其自传白描《五柳先生传》中,陶潜不仅把自己描绘成嗜酒之士,而且在《拟挽歌辞》中他还表达了已不能再饮的遗憾。确实,这也就是为什么陶潜作为一个嗜酒之士和“无忧无虑”的隐士为人仰慕的道理。唐代诗人王维称颂陶潜性格的任真及其与酒的关系(“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宋代诗人欧阳修自称“醉翁”,也显然是受了陶潜的影响。偶尔有些批评家如清代的冯班等人,批评陶潜的嗜酒癖。不过,总的来说,陶潜作为一个淳朴的饮酒者的形象在中国诗的读者心目中已牢固树立。值得一提的是,传统中国诗歌中所说的酣醉并不一定意味着酒鬼的贪杯,而更像是灵感的激发。然而,与这些陶氏饮酒诗的字面阅读相并行的是一种更强的隐喻诠释的传统,它最终有助于巩固陶潜的经典地位。早在六朝时代,萧统在他编辑的《陶渊明集》序中便已指出:“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寄酒为迹也。”[26] 究竟这“寄酒为迹”是指什么,萧统语焉不详,但在萧氏影响之下,后代的批评家开始将陶潜视作不是单纯爱喝酒的诗人,而是某个以饮酒为面具掩饰深意的人。陶氏有名的20首《饮酒》诗的情形便是如此,它并不真是关于饮酒本身而可能是意在政事,正如组诗的结句所传达的信息:2018年,孙康宜在宇文所安退休会上,孙康宜致辞并朗诵赠诗这里,诗人明显是在以醉为借口来传递某种严肃的意味。正如詹姆士·海陶尔(James Hightower)所指出的,这些诗句一直是“儒家诠释者所乐于称道的”,因为诗人宣称即使他放纵狂饮,“那也显然只是对时代之险恶的绝望,而不是对礼教本身的弃绝”[27] 。鉴于中国的笺注者多爱将诗“时代背景化”这一事实,可以想见他们多么热衷于将陶潜的《饮酒》诗在历史事件中予以坐实。对于许多笺注者来说,陶潜诗中所暗示的所谓“时代之险恶”一定是指他拒绝出仕的刘宋王朝。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解读可以被视作是沈约将陶潜塑造为晋朝忠贞不贰之臣的延伸。沈约在其《宋书·隐逸传》中点明,尽管陶潜在晋安帝义熙年间(405—418)之前采用晋代年号来纪年,而自刘宋王朝之后便改用天干地支(甲子)来纪年——一个似乎为诗人之忠贞作见证的机关[28] 。虽说沈约的话自有其偏见及自身的意识形态,并因此在某些笺注者看来并不牢靠,然而它自宋代以来成了诗评家解读陶诗的基本依据。对于中国的批评家来说,再没有其他的阐释方式更令人信服的了。确实,后来此类隐喻解读对于新朝的遗民来说是特别有效的阐释手段。其中最有力的佐证是宋代爱国主义者文天祥,他在《海上》一诗中称赞陶潜以醉为其忠君的幌子(“陶潜岂醉人”)——在当时文天祥自己也为王朝变迁这同样的问题所迫。对文天祥而言,陶潜之饮代表了一种理想的手段或面具,使他在说某一事情时却暗指另一件事;萧统所说的陶氏之饮另有所指,在文天祥的反馈中找到了圆满的答案。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同意这样的隐喻解读,然而在陶潜之饮的背后寻求深意的总的努力方向却鼓动了多少代学者将陶潜视作一个更复杂的人物,一个知道在其诗中如何在自我亮相和自我隐藏之间做出抉择的人物。例如,现代作家鲁迅在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强调宁静的超越与积极的政治参与两者在陶潜身上并存。同样,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以为陶氏之饮对于当时腐败的政局来说,既是逃避又是抗议[29]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现代学者——诸如梁启超和朱光潜——开始对将陶潜看成是晋代遗民这种说法提出质疑[30]。某些学者甚至强调陶潜曾在刘裕(刘宋王朝的开国者)手下任过职这一事实,而这一事实排除了陶潜乃晋室忠贞不贰的遗民之可能性[31]。而另一些人则发现一些被当成政治隐喻来解读的陶潜诗作居然作于晋室倾覆之前,这样一来,它们就不能算作遗民之作了[32] 。所有这些对陶氏的新解读都会使得人性的复杂性和艺术与现实间的沟壑明朗化。
 另一个陶潜之谜是那个从不沾染女色的正人君子形象。也许是这个道理,陶氏挖掘性爱主题的《闲情赋》对许多传统和现代学者来说便成了一个问题。问题之一便出自萧统,陶潜作品的第一位编纂者,也是第一位批评《闲情赋》“白璧微瑕”的批评家[33] 。尽管道德方面的考量在萧统的褒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我想这篇赋本身就像淫靡的宫体诗那样包含了女性化的话语这样一个事实,也可能因此导致了他的评价。不管怎么样,由于萧统的批评,在长达数百年间无人敢再对此妄议,直到宋代的苏轼(被公认为陶潜最大的追随者),才开始重新审视这篇长期遭人冷落的作品。与但愿《闲情赋》不曾存在的萧统有所不同,苏轼将它视作卓绝的篇什,其价值可与《诗经》和屈骚相比拟,于是苏轼在他为《文选》所作的跋文中写道:《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34]。苏轼的见解后来博得了清代著名学者陈沆的首肯,后者也称陶氏的《闲情赋》是晋代最伟大的篇什[35] 。苏轼以为在《闲情赋》中最可贵的是“真”,这在苏轼看来是陶潜诗艺的秘诀[36] 。诗中求“真”意味着传达心声,虽说它也是通过假面的设置来达成的。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真”,陶诗才能开启人的情感,它既真切又费解,既静穆又狂放。确实,有了《闲情赋》,陶潜似乎才达到了一个练达的新境界,因而也就是一个高难成就的新境界。这样一个“成就”包含了各种主题和风格实验的成功糅合。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轼说陶潜之诗“质而实绮”[37] ,这对常见的讥贬陶诗“质朴”之词是一个绝妙的驳斥。好在许多现代学者都能领会苏轼对《闲情赋》的重新评价,并继续提供新的解读方式。例如,梁启超曾如此称赞陶潜的“言情”技巧:集中写男女情爱的诗,一首也没有,因为他实在没有这种事实。但他却不是不能写。《闲情赋》里头,“愿在衣而为领……”底下一连叠十句“愿在……而为……”,熨帖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艳句,也很少比得上。因为他心苗上本来有极温润的情绪,所以要说便说得出[38]。此外,朱光潜在《诗论》的“陶渊明”一章中也为陶潜以传神之笔状“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深为折服。同样,鲁迅在《题〈未定草〉》中也褒奖陶潜有勇气挖掘性爱各层面,使之读上去几乎像一篇自白。所有这些现代学者的评语都代表了一种轨迹:逐步扬弃隐喻解读——包括扬弃苏轼那种诉诸《诗经》的道德权威——而趋向更变幻莫测、更深入人意、更丰富、更实在的解读。结果是,当我们欣赏文本本身时,一个更具人情、更可信的诗人陶潜的形象便浮现出来。不过,我在这里应当补充的是,事实上,早在明朝,钟惺之类的批评家已经开始探测陶潜诗艺的复杂性[39]。尤其是孙月峰声称陶诗“真率意却自练中出,所以耐咀嚼”[40] ,因而其平易的印象也只不过是假象而已。与陶氏平淡诗风之谜紧密相连的,是一个为自己的小庭院和田园生活所陶醉而怡然自适的隐士。陶潜是否曾为他决定退居后悔过?他是否有时候也想过另外一种生活?我们已看到自清代以降,批评家开始质疑陶潜作为一个隐士的单纯性——例如19世纪诗人龚自珍在《舟中读陶诗·其二》中把陶潜当成有经世之抱负的豪杰之士,可与三国时代的诸葛亮相比:很显然龚自珍并没有把陶潜当作一个平淡的人。对龚氏及其同时代人而言,陶潜代表了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有出仕的凌云之志却扼腕而弃之——都是因为生不逢时。他们相信在陶潜身上有一股孤立无援之感,尽管很微妙,却是报效无门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型特征。而这一微妙的落寞感正是陶潜对鲁迅如此有魅力的地方。有一点几乎所有的陶学学者都忽略了——直到近来学者李华才提醒我们,那便是这样一个事实:早在唐代,诗人杜甫便已对陶潜作为一个恬然自乐的隐士形象提出质疑。但不幸的是杜甫之言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误读,而他对于陶氏的见解也遭误解。这也就是杜甫在其《遣兴五首·其一》中所说的有关陶潜的话:据李华所说,杜甫在这几句中要传递的是这样的信息:“陶渊明虽然避俗,却也未能免俗。何以知之?因为从陶的诗集来看,其中很有恨自己一生枯槁之意。”[41] 这里,李华将杜甫诗中的“枯槁”解作“穷困潦倒”是很有理由的,因为陶潜在他自己的第11首《饮酒》诗中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之窘迫:李华以为,陶潜在指出颜回为其身后浮名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同时,或许也在针对他自身的潦倒做自嘲。这也自然可以联想到杜甫在提到陶潜时,也会有一副自嘲的口吻。因此,当杜甫在试图揭开陶潜的面具时——以一个甘于清贫的理想隐士的面目出现的所谓“陶潜”,杜甫实际上也在做自我曝光。确实如此,杜甫终其一生穷愁潦倒,也自然而然会自比陶潜。有鉴于此,浦起龙在评解杜甫《遣兴》时指出:“嘲渊明,自嘲也。假一渊明为本身像赞。”[42]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杜甫在他的诗作中一再提到陶潜,而实际上,正是杜甫第一个将陶潜提升到文学上的经典地位[43]。
另一个陶潜之谜是那个从不沾染女色的正人君子形象。也许是这个道理,陶氏挖掘性爱主题的《闲情赋》对许多传统和现代学者来说便成了一个问题。问题之一便出自萧统,陶潜作品的第一位编纂者,也是第一位批评《闲情赋》“白璧微瑕”的批评家[33] 。尽管道德方面的考量在萧统的褒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我想这篇赋本身就像淫靡的宫体诗那样包含了女性化的话语这样一个事实,也可能因此导致了他的评价。不管怎么样,由于萧统的批评,在长达数百年间无人敢再对此妄议,直到宋代的苏轼(被公认为陶潜最大的追随者),才开始重新审视这篇长期遭人冷落的作品。与但愿《闲情赋》不曾存在的萧统有所不同,苏轼将它视作卓绝的篇什,其价值可与《诗经》和屈骚相比拟,于是苏轼在他为《文选》所作的跋文中写道:《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34]。苏轼的见解后来博得了清代著名学者陈沆的首肯,后者也称陶氏的《闲情赋》是晋代最伟大的篇什[35] 。苏轼以为在《闲情赋》中最可贵的是“真”,这在苏轼看来是陶潜诗艺的秘诀[36] 。诗中求“真”意味着传达心声,虽说它也是通过假面的设置来达成的。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真”,陶诗才能开启人的情感,它既真切又费解,既静穆又狂放。确实,有了《闲情赋》,陶潜似乎才达到了一个练达的新境界,因而也就是一个高难成就的新境界。这样一个“成就”包含了各种主题和风格实验的成功糅合。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轼说陶潜之诗“质而实绮”[37] ,这对常见的讥贬陶诗“质朴”之词是一个绝妙的驳斥。好在许多现代学者都能领会苏轼对《闲情赋》的重新评价,并继续提供新的解读方式。例如,梁启超曾如此称赞陶潜的“言情”技巧:集中写男女情爱的诗,一首也没有,因为他实在没有这种事实。但他却不是不能写。《闲情赋》里头,“愿在衣而为领……”底下一连叠十句“愿在……而为……”,熨帖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艳句,也很少比得上。因为他心苗上本来有极温润的情绪,所以要说便说得出[38]。此外,朱光潜在《诗论》的“陶渊明”一章中也为陶潜以传神之笔状“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深为折服。同样,鲁迅在《题〈未定草〉》中也褒奖陶潜有勇气挖掘性爱各层面,使之读上去几乎像一篇自白。所有这些现代学者的评语都代表了一种轨迹:逐步扬弃隐喻解读——包括扬弃苏轼那种诉诸《诗经》的道德权威——而趋向更变幻莫测、更深入人意、更丰富、更实在的解读。结果是,当我们欣赏文本本身时,一个更具人情、更可信的诗人陶潜的形象便浮现出来。不过,我在这里应当补充的是,事实上,早在明朝,钟惺之类的批评家已经开始探测陶潜诗艺的复杂性[39]。尤其是孙月峰声称陶诗“真率意却自练中出,所以耐咀嚼”[40] ,因而其平易的印象也只不过是假象而已。与陶氏平淡诗风之谜紧密相连的,是一个为自己的小庭院和田园生活所陶醉而怡然自适的隐士。陶潜是否曾为他决定退居后悔过?他是否有时候也想过另外一种生活?我们已看到自清代以降,批评家开始质疑陶潜作为一个隐士的单纯性——例如19世纪诗人龚自珍在《舟中读陶诗·其二》中把陶潜当成有经世之抱负的豪杰之士,可与三国时代的诸葛亮相比:很显然龚自珍并没有把陶潜当作一个平淡的人。对龚氏及其同时代人而言,陶潜代表了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有出仕的凌云之志却扼腕而弃之——都是因为生不逢时。他们相信在陶潜身上有一股孤立无援之感,尽管很微妙,却是报效无门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型特征。而这一微妙的落寞感正是陶潜对鲁迅如此有魅力的地方。有一点几乎所有的陶学学者都忽略了——直到近来学者李华才提醒我们,那便是这样一个事实:早在唐代,诗人杜甫便已对陶潜作为一个恬然自乐的隐士形象提出质疑。但不幸的是杜甫之言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误读,而他对于陶氏的见解也遭误解。这也就是杜甫在其《遣兴五首·其一》中所说的有关陶潜的话:据李华所说,杜甫在这几句中要传递的是这样的信息:“陶渊明虽然避俗,却也未能免俗。何以知之?因为从陶的诗集来看,其中很有恨自己一生枯槁之意。”[41] 这里,李华将杜甫诗中的“枯槁”解作“穷困潦倒”是很有理由的,因为陶潜在他自己的第11首《饮酒》诗中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之窘迫:李华以为,陶潜在指出颜回为其身后浮名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同时,或许也在针对他自身的潦倒做自嘲。这也自然可以联想到杜甫在提到陶潜时,也会有一副自嘲的口吻。因此,当杜甫在试图揭开陶潜的面具时——以一个甘于清贫的理想隐士的面目出现的所谓“陶潜”,杜甫实际上也在做自我曝光。确实如此,杜甫终其一生穷愁潦倒,也自然而然会自比陶潜。有鉴于此,浦起龙在评解杜甫《遣兴》时指出:“嘲渊明,自嘲也。假一渊明为本身像赞。”[42]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杜甫在他的诗作中一再提到陶潜,而实际上,正是杜甫第一个将陶潜提升到文学上的经典地位[43]。
孙康宜、哈罗德·布鲁姆和学生(1998年12月2日)
然而问题是,正如李华所指出的,在过去的数世纪内批评家一直在误读杜甫,实际上这是对杜甫解读陶潜的误读。由于批评家常将“枯槁”解作“风格上的平淡”,他们自然而然会认定杜甫以其《遣兴》一诗来批评陶潜的诗风。这种误解导致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其《诗薮》中以为“子美之不甚喜陶诗,而恨其枯槁也”[44] 。 后来,朱光潜也沿袭了胡应麟的说法。直到1992年李华出版其专著《陶渊明新论》,学者才开始重读杜甫。这一有趣的误读实例证实了我们的想法,即经典化的作者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流程中的读者反馈的产物。据我们所知,陶潜其实是很在意读者反馈的那样一种人,正如他在其《饮酒》组诗序中所言,他让朋友抄录其诗作(“聊命故人书之”)。尽管陶潜在说这话时用了一副谦逊的口吻——不过是为博得朋友的“欢笑”而已,毫无疑问他还是很在乎他作品的流传。而且,正如戴维斯所指出的,陶潜同其他许多中国诗人一样都在“营造自我的形象”。对读者而言,陶潜自我形象中永葆魅力的一个侧面就是他对自己的诚实,即便在他惶惑的时候他也没有违拗自己的良心——甚至是在他饥寒交迫时:……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正是靠这份自我的挖掘,陶诗的读者才使得他们自己与诗作间有亲密无间之感。故而许多读者在窘迫之际便自然而然地转向陶诗求助,为他们个人的困苦找寻一个满意的答案。于是,梁启超抱病在身时所读的不是别的,而正是陶诗,因而抛出了他的著名的《陶渊明年谱》。20世纪30年代抗战期间,李辰冬在自家田舍间勤勉地研究陶诗,结果完成了发人深思的陶学著作《陶渊明评论》。当然,也有读者只是把读陶诗当作消遣,诸如丁福保以日诵陶诗而自娱。丁氏为陶集编订了20多个版本,最终据宋珍本作《陶渊明诗笺注》而知名[45]。诚如宋代词人辛弃疾在《水龙吟》中所言:“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不错,总的说来读者对陶潜的生平颇感兴趣,不过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有更多的读者着迷于陶潜对自己死亡的思索。事实上,没有作家能像陶潜那样带着一份自觉意识来关注现实、达观和死亡——像他的《挽歌诗》及《自祭文》。下面一段话应为陶氏临终前不久的绝笔,它只能是出自这样一个人之手,即他对人的有尽天年虽有疑惑,却又找到了终极的答案:乐天委分,以致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于今斯化,可以无恨。像这样的一副笔墨,写来为自己作“挽歌”,在陶潜那个时代恐怕是史无前例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古来忠臣烈士慷慨就死时几句简单的绝命诗词,虽然常有,若文学家临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除渊明外像没有第二位哩。[46]
当然,陶氏之言,是否可做字面理解,即它是否确系他的临终绝笔,恐怕永远也无法肯定。但毫无疑问许多读者仍然相信这是陶氏的绝笔。据信也正是在陶潜的影响之下,日本诗集《万叶集》收录了《挽歌》部以及其他一些像是模仿陶氏预见自己死亡的歌谣[47]。有趣的是,也许正是在陶潜的临终篇什中,读者才发现修史者对诗人的传记描述与陶潜的自我描述正相吻合。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所描述的陶潜的“视死如归”也印证了诗人为自己所做的描绘[48] 。 这正是陶氏希望为后人所记取的他的自我形象。然而,他在这篇绝笔祭文的篇终还是禁不住向读者流露出他的无奈感:确实,陶氏最后这番话是一位经典诗人复杂而隐秘的自我告白。[1][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经典》(<i>The Western Canon</i>,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第27页。
[2]见方回的组诗《诗思》中的一联:“万古陶兼杜,谁堪配飨之?”
[3]钟优民《陶学史话》,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6、139、155页。
[4]参见梁启超《陶渊明》,1923年首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年重印。近来叶嘉莹也对此表示赞同,见叶嘉莹《陶渊明饮酒诗讲录》,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37页。
[5]钟优民《陶学史话》,第7页。
[6]有关这一点,王国璎有一段极富洞见的讨论,见其《史传中的陶渊明》,载于《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2000年5月),第200页。
[7]王定璋《陶渊明悬案揭秘》,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8]见梁启超《陶渊明》,第45—77页。
[9]据古直的说法,陶潜生于376年,终年52岁。见古直《陶渊明的年纪问题》,载于《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
[10]A. R. Davis, <i>Tao Yuan-ming (A. D. 365-427);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s </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Vol.1, p.2.
[11]见Kang-i Sun Chang, <i>Six Dynasties Poetry</i>, pp.3-14。
[12]Davis, <i>Tao Yuan-ming</i>, Vol.1, p.2.
[13]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第207—208页。
[14]同②,第216—2
[15]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第216—228页。
[16]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55页。
[17]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77页。
[18]参见Davis, <i>Tao Yuan-ming</i>, p.4。
[19]Stephen Owen, “The Self’s Perfect Minor: Poetry as Autobiography”, Shuen-fu Lin and Stephen Owen eds., <i>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i>á<i>ng</i>(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第214页。
[21]参见王国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论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245、264、323—350页。又见陈永明《莫信诗人竟平淡——陶渊明心路新探》,台北:台湾书店,1998年版,第75页。
[22]参见萧统《陶渊明传》,陶澍笺注《陶靖节集注》,台北:世界书局,1999年版,第17页。
[23]钟优民《陶学史话》,第382页。
[24]参见布鲁姆所著《莎士比亚:人的创造》(<i>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i>)<i> </i>(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在该书中他说在一定程度上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
[25]沈约《宋书·隐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6页。
[26]萧统《陶渊明集·序》,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年版,第4页。
[27]参见[美]海陶尔《陶潜的诗》[<i>The Poetry of Táo Chíen </i>(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第115页。有关这几行诗的讨论,参见叶嘉莹《陶渊明饮酒诗讲录》,第225—233页。
[28]参见陶澍笺注《陶靖节集注》,第16页。
[29]参见朱光潜《诗论》第13章。
[30]参见梁启超《陶渊明》,第5—6页。
[31]例如宋云彬《陶渊明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载《新中华副刊》6卷3期(1948年2月),引自钟优民《陶学史话》,第183页。
[32]例如李辰冬《陶渊明评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2页。
[33]萧统《陶渊明集·序》。
[34]苏轼《题文选》,见钟优民《陶学史话》,第61页。
[35]参见陈沆《诗比兴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钟优民《陶学史话》,第151页。
[36]参见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见钟优民《陶学史话》,第46页。
[37]参见苏轼《与苏辙书》;李华《陶渊明新论》,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38]梁启超《陶渊明》,第13页。
[39]参见钟惺《古诗归》中对陶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一诗的批语。
[40]孙月峰《文选瀹注》卷13。
[41] 李华《陶渊明新论》,第227—228页。
[42] 浦起龙《读杜心解》,引自李华《陶渊明新论》,第228页。
[43] 邓杜梁《唐宋诗风——诗歌的传统与新变》,台北:台湾书店,1998年版,第18页。
[44] 胡应麟《诗薮》,引自李华《陶渊明新论》,第227页。
[45] 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1927年版;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重印,第3页。
[46] 梁启超《陶渊明》,第38页。
[47] 参见王定璋《陶渊明悬案揭祕》,第244页。有关陶潜对《万叶集》的影响的实例,见《万叶集》,第486页。
[48]参见王国璎《乐天委分,以致百年——陶渊明〈自祭文〉之自画像》,原载于《中国语文学》34辑(1999年12月),第323—340页。
孙康宜,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原籍天津,1944 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往台湾。1968 年移居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荣休讲座教授,曾获美国人文学科多种荣誉奖金,中英文著作多种。2015 年4 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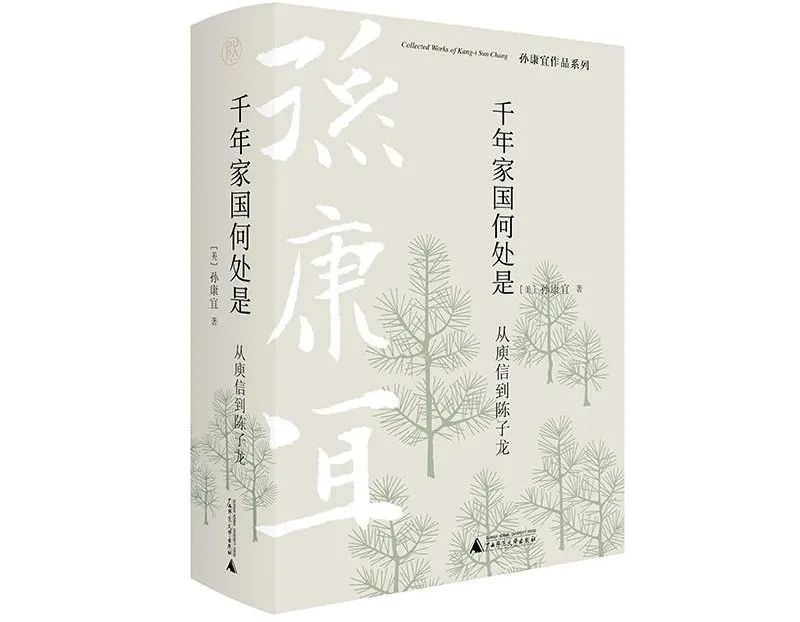







![[强]](https://res.wx.qq.com/mpres/zh_CN/htmledition/comm_htmledition/images/pic/common/pic_blank.gif)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名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