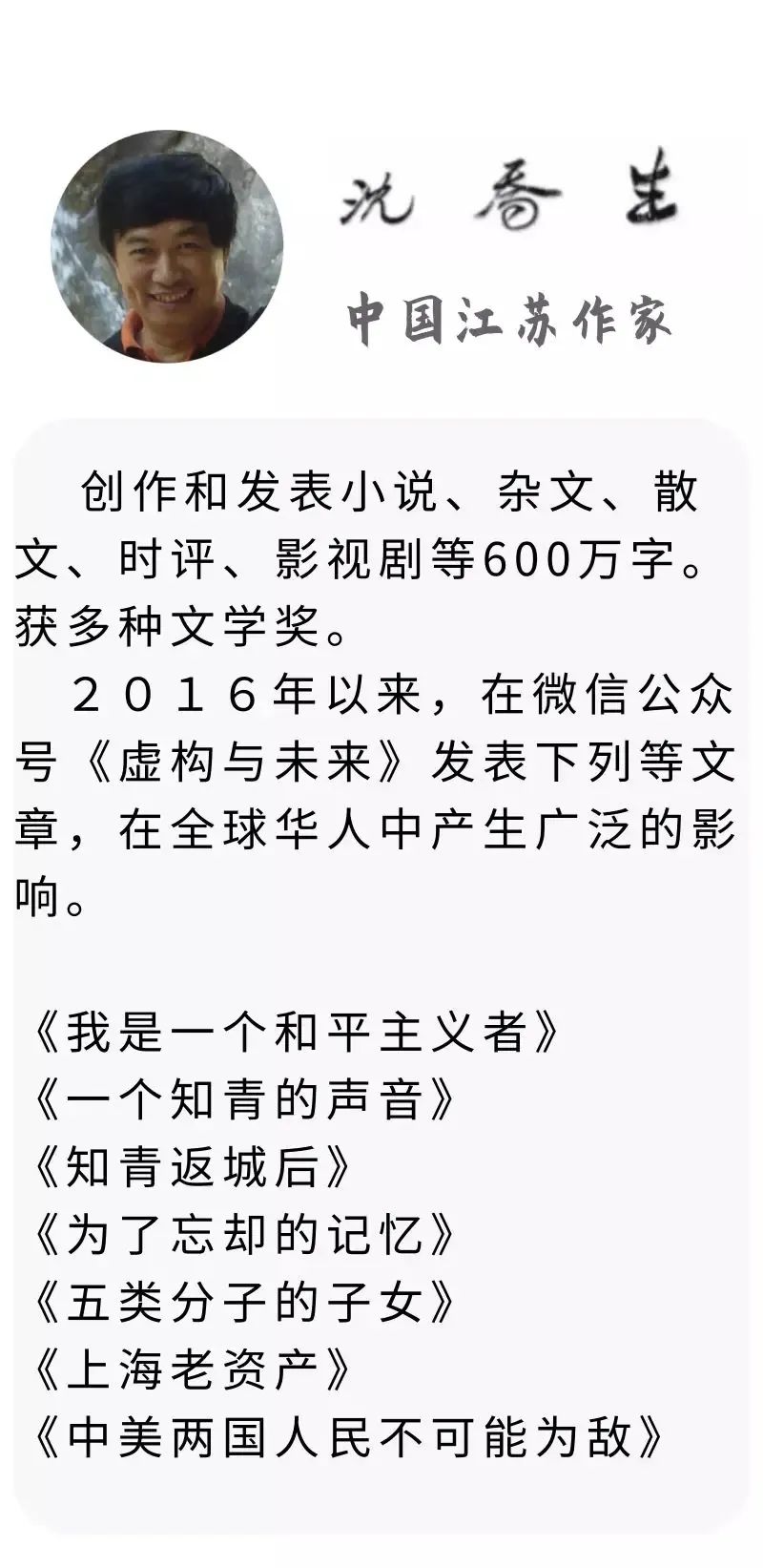![]()



将我的博客复制一份至《海外博客》
由于数据量较大,请您耐心等待复制完成
复制

正文
沈乔生|上海是一条流经世界的江
(2022-04-25 14:08:59)
下一个
上海不是一条河,上海是一条江。还不止一条江,上海头枕长江,黄浦江从她的腹部流过,两江汇合,在吴淞口流入大海,流向世界。
上海开埠不到200年,但是,她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东方大国腰部一颗璀璨的明珠,光耀世界。多少上海人,尤其是老上海,特别喜欢回忆上海的过往,所有世俗、平凡的生活在他们痴醉的回忆中,都似蒙上纱巾一样曼妙多姿,甚至连生炉子、倒马桶这类粗活,都变得温情脉脉,颇有田园风光。有的人特别青睐上海的早点,大饼油条、咸豆浆、糍饭糕、排骨年糕、擂沙圆、生煎馒头……他们数说起来,口内生津;有的人热衷于民国建筑和历史,而上海则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于是,上海名人、文坛巨擘、梨园春秋、上海大亨、外国冒险家、上海大流氓等等,出现了无数虚虚实实、充满想象力的篇章。
上海这条江流经世界,许多上海人也随之来到世界各地,他们劳作、生存,有一天,他们发现,上海和他们居住的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罗马、温哥华、悉尼、马德里等等大城市比,上海一点都不差,某种意义上,上海更多一些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愫。
尤其是近三十年,上海矗起了无数美丽奇幻的高楼大厦,更使人浮想联翩。有一天,我来到某幢大厦的顶楼,望出去,四周的高楼就像儿童玩的红红蓝蓝的积木,拥有这些,上海人怎么会没有荣耀和虚荣呢?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他们的上海,我们的上海》,细说上海人的处世的特点和长处。而现在,我也困惑了。我和上海相熟相知一辈子了,什么时候看见她像今天这样?
城市是有灵魂的,没有灵魂的城市不能称为城市,最多称为寄身地。
城市的灵魂是什么?是在人们交往最纷繁复杂的地方,却依然有人性,有温度。
我写过一文,对上海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做点评,文章存活不足三小时。
昨天看见一个视频,一个母亲悲伤、愤懑的呼救声。她的9岁的女儿胸前生出一个包,她带着女儿去看病,在医院外呆了整整一夜,视频上,女儿穿着防护服,盖着衣服,而她在边上陪了一夜。而天亮之后,她又被告知,无法替她的女儿看病。她发出撕裂人心的呼喊,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女儿不能就医,就眼睁睁看着病情发展?在场的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回答她。9岁的女儿睁着一双无辜、疑惑的眼睛。
上一篇文章,我就点评了铁链锁门,主人叫起来:“着火怎么办?”现在更有甚者,不少小区,高楼的出入口都筑起了铁丝网,把整幢楼的人都封在里面。住家自嘲说,这里是野生动物园。
有个视频,一个老太完全站不住了,两个大白一个护工,三人抱头抬脚,把老太扛起来,扛上大巴,送去隔离。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面对种种不合理做法,许多工作人员也深怀内疚,他们对民众说,你问我,我去问谁?我已经无数次反映上去,没有人回答我,实在抱歉,我也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的哀鸣。
那么,是在哪个环节使上海的灵魂黯淡,失去人性?是什么突然的外力,打断了上海人情感上的内在链接?
无论执行什么天大的政策,都存在一个人性的问题,不是显示人性的善,就是暴露人性的恶。
当年,希特勒在欧洲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一艘又一艘轮船驰进上海港,船上挤满犹太人。他们向世界呼救,只有上海接纳他们。但是,迫于德国的淫威,上海当局还是把他们圈起来,筑起高墙,不让他们外出。他们缺吃少穿,这和上海人当下面临的有点像。
犹太人饥饿、苦闷,这时,就有上海民众的壮举,不知谁领的头,把面包、把蔬菜,把饼干扔过墙去,犹太人的眼睛亮了,他们饥肠辘辘的腹中有食物了。一个人,两个人,许多人都加入这个行列。一天,两天,持续许多天。这是上海历史上人性灿烂的一页。我幼年时不知道这个故事,成年后听说,加深了我对上海的热爱。
今天,我也寻找光明,在抗疫中,每一点人性的光芒和温暖,我都会极力赞美。
那种用铁链强行锁门的做法是恶劣的,现在某些地方却变本加利,发展到用铁网封门;那种把90多岁的老人送进方舱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那种把大人送去隔离,把2岁的孩子扔在家中也是错的,丧失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基本的传统美德;那种使危急病人无处看病以至贻误病情死亡、病人跳楼等更是错的,即使是局部现象也不能容忍,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这不仅造成远比新冠严重的次生灾难,而且把我们近几十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法制破坏掉,重新践踏在地!某些大白对民众粗暴、野蛮的做法也是不能容忍的,即使是少数人,也是不能接受的,它会引起人们对某些历史罪恶行径的多重联想,极可能把潘多拉盒子里的恶魔重新释放出来!
有人发给我一个帖,是批评上海的,说全国人民驰援上海,他们不但不感恩,却只顾自己,只是喊饿,非常自私。
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难道没有吃食,忍饥挨饿还不能呼喊?难道有急病看不上,绝望之极从楼上跳下来,旁边的人还不能为他呼救?难道家门无端地被铁链锁住,被铁笼罩住,身陷恐惧,还不能求救?
坦白地说,迄今为止,上海人所做的一切,只是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呼喊,为他们被无理剥夺的正当权利抗争!他们是被逼得无路才发声的。他们无畏的行为使粗暴的做法遭受了挫折,而其他城市鲜有这么做,这就是上海的意义!
我们必须承认,上海人所有的呼救,都是生存的呼救,是最基本的诉求,是为了活着不可或缺的要求,它们是悲戚的,也是动人心魄的。然而,如果进一步问,我们的呼救只能是最基本的请求,跪在地下,只是为了吃,那么,还是愧对先人的。一百多年的五四,都要引进德先生、赛先生,而我们今天只能为饥饿呐喊,为生病求救,叫人说什么好?
近来,上海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简单讲,一个无耻、投机的家伙,说被人打了,被踢了裆。沪上无数人都喜形于色,有的还为自己没有赶上而抱恨。很快又有消息传出,说没有打,只是欠揍。但闻者不觉得遗憾,还是和被踢了裆一样普大喜奔。打和不打效果都一样。
一个人活到这个地步,编一个虚假信息,就被人憧憬一番,喜乐一番,一定不是滋味。
这和南宋的秦桧有点像,秦桧活着没有来西湖跪过,可是死后就有好事者来搞创作。如这家伙以后也被人造一个形象,打肿了眼睛,踢了裆,放在什么风景地方,有点搞笑了。
童年时候,我住在上海的福州路和湖北路的交叉口。以前,二马路三马路都是妓女出没的地区。后来福州路成了书店一条路。大概在1968年,我遛跶进一家书店,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样的人把一大叠英文词典放在柜台上,里面有不少精装本,硬封面的。书店里的收书的人翻了翻,对他说:“12元。”
那个人像被烫伤一样,说:“还能加点伐?”书店的人冷漠地摇头:“现在还有多少人要词典?卖不掉的。”那戴眼镜脸上就有难看的颜色,也许这些辞典跟他一辈子了,哪能轻易割舍,但12元钱也能维持他一段时间的生活。
这段记忆插在我的大脑中,没头没脑,但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不难解读。
这地段有许多饭店,杏花楼、大鸿运、王宝和、老半斋等等。一个个名字都富有个性。我有个武断的说法,名字没有个性,做不出好饭店。上海从来是个讲究吃的地方。酱汁肉、宁波汤团、蠔油牛肉、葱油鸡、古佬肉,是我幼时的所爱。
穿过浙江路,就是南京路了,迎面是永安公司,隔条小马路(我忘记名字了)西面是我父亲的华新公司,后来改名叫金桥。有段时间,我成天在这里玩。我当然不会知道,当时上海的最高首长每天照例问的是,昨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
我记住了父亲写检查时苦恼的脸,也记住他被新雅饭店的美食短暂地映红的脸,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老爸终于没有成为空降部队。
穿过湖北路,就到人民广场,这是上海最开阔的地方,以前是跑马厅。后来它成为历次革命群众聚集的大场所。记得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有次我也在人民广场上,不知怎么会来的。满目都是造反派的旗帜,都是大卡车,车上站满拿着铁棍、长矛的年轻工人。我当时是初中生,很羡慕,也搞不懂,以为是翻天覆地的伟大举动,后来才知道是小丑做怪。
它们都是上海的历史,是上海的一个局部。人性和非人性,人性和反人性,都在这里反复纠缠、斗争。
上海是一条绵延、亘古的江,当下疫情只是她的一个弯。
今天我不住在上海,但在我遥远的童年时期,上海啊,你就编织了我的生命密码,从此影响了我的一生。
上海是一条江。来到外滩,隔着一条黄浦江,对岸是浦东,是近四十年建起的奇幻建筑,东方明珠、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金茂大厦是代表。浦西则是享誉中外的外滩,我去纽约的华尔街看过,两者的风格相似。外滩大楼的外墙都是大块花岗岩的,威严、结实、深沉,超过百年了,没有丝毫陈旧的感觉,它们象征了那段历史。和平饭店、海关大楼是它们的代表。海关大楼的钟声时时敲响,是上海脉搏的跳动。
陆家嘴和外滩隔江对视,是历史和现代的对视,是前辈和当下人的对视,是文明的包容和包容的文明的对视。两岸都在凝视着上海,凝视着黄浦江,看它流向哪里,看她怎么流!
黄浦江,是我的母亲河。我诧异,很少听到有上海人叫黄浦江母亲河的,大概她流经的地域不广,历史不久,来源太多太混杂,可这就是上海,上海就是这个特点!
这条江流向世界,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将如何装饰她,让她流动的时候,载着人性,载着文明,还是载着其他?